冰刀破冰,热血将至!当米兰冬奥会的激情燃

亲爱的朋友们: 无论你此刻身处世界的哪一端,站在怎样的人生阶段,正经历着什么,我都想先与你们分享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感受: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持续动荡的大时代。世界的边界在改变,秩序在重组,迁徙与不确定性,几乎成为一种日常背景。在这样的时代里,个体的生命常常显得渺小而脆弱,仿佛随时可能被历史的洪流卷走、覆盖,甚至被迅速遗忘。
正是在这样的洪流中,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:当一切都在流动时,人究竟靠什么站立?靠什么而让我们精神不倒?当人生的意义被反复思辨,我们又如何继续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?
过去几年,我一直在思考、写作与行走。从上海出发,重返日本与北美,常去欧洲甚至更远的北极。旅行中从未停过笔,写苦难、离散;写信仰、人性……无论写什么,多么悲催,都能在黑夜里找到星光。
此刻,我走进了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世界——当年日本新潟县的越后汤泽地区。缘于文学作品的震撼,那种虚无之美、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,令人怦然心动,又惆怅不已。川端的唯美意象描写融入至人物情感的表达之中,让我仿佛成为书中的人物。我会在这里度过一段漫长而安静的时光。雪覆盖了一切声音,也覆盖了许多熟悉的意义结构。世界仿佛被还原成最简单的存在状态:时间在流逝,生命在呼吸。在如此环境中,我第一次直接地感受到一种真相:生命本身,并不天然携带意义。它被抛入世界,被暴露在历史、制度、偶然与命运之中,像一颗无法命名的种子。但也正是在这份“被抛入”的状态中,我理解了另一层深意——生命没有被预先赋值,它才拥有被人承担、被人完成的尊严。意义不是赠予,而是实践;不是奖赏,而是回应。不辜负此生,并不是因为人生已经被证明“值得”,而是因为它已经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上。
在雪国的沉静中,我不断想到那些被时代洪流卷走的人。他们并非历史的主角,却承受着历史最直接的重量。他们在磨难中生存,在信仰的裂隙中坚持,在被世界暂时遗忘的角落里,努力维持作为人的形态。
这让我更加确信:真正承载时代重量的,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,而是具体而脆弱的生命。时代可以被反复书写,但人的经验一旦被抹去,便不再复返。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,我始终无法忽视这种具体的、身体性的存在。女性的书写,往往更接近生命的原貌——不抽象、不宏大,却真实、细微、持久。它关心存活本身,关心如何在破碎中继续照料他人,也照料自己。
我常被问,文学究竟能为苦难做什么。我的回答始终艰难,文学不能阻止、也无法替代、但真正的文学至少可以勇敢、可以治愈、可以拒绝麻木、可以鼓舞人心。
人类的苦难,并不只是发生本身,而是被迅速简化、归档、遗忘。当一个人只被称为数字、案例或背景,他的尊严便已消失。文学所能做的,是把名字还给人,把具体的生命重新带回公共视野。文学不是为苦难寻找意义,而是证明:人在苦难中,并未彻底被取消。哪怕只是被阅读、被理解、被记住,孤独便不再是封闭的。
世界文学中,关于祖国与故乡的书写,几乎贯穿了人类精神史。流亡、漂泊、他乡,随后在漫长的试炼之后,寻找返乡的道路。这种“返乡”,从来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抵达,更是一种精神的凯旋。它意味着,在世界的暴力、诱惑与虚无之中,个体仍然保有内在的坐标。对我而言,祖国是文化与生命的根系,而故乡更像母亲。无需反复证明,却始终存在。无论我身在何处,我都能听见故乡河流的声音,它在时间深处流动,提醒我来处,也提醒我责任。
正因为热爱,我无法在不公与失序面前保持沉默。沉默并非中立,而是一种放弃。写作者如果在真理面前退后,文学关于正义的讨论便会失去底线。
这些年,我不断尝试让文学进入音乐,进入歌剧、交响乐与音乐组诗。当语言无法承载全部经验时,音乐可以继续说话。文学与音乐并不是逃离现实,而是一种疗愈,让破碎的经验重新获得节奏,让孤立的灵魂意识到:它并不独自承受。
亲爱的读者朋友们,如果你正经历失望,甚至绝望,请相信,光明并不遥远。它或许微弱、迟缓、安静,但它真实存在,存在于你仍然选择不放弃的那一刻。在这个不断取消意义的时代,正是生命本身的“无意义”,赋予了我们继续拥有意义的自由。只要我们仍然愿意承担,仍然愿意关怀,仍然愿意成为人,精神的彼岸就不会消失。
谢谢你们。 祝新春安好。
附录:
作家贝拉的核心思想母题在全球流动时代,以文学为“裸露的生命”重新赋名。贝拉的写作,立足于全球化时代的流动经验,长期关注在战乱逃亡、迁徙、制度失序与历史暴力中被边缘化的个体生命。她的文学实践并不追求宏大叙事的完整性,而是将目光持续投向那些被历史经过、却未被历史收录的人。在她的作品中,文学通过命名、记忆与共感,使生命重新进入人类经验的共同空间。
“裸露的生命”被抛入世界。贝拉的写作反复呈现一种处境:个体生命被抛入世界,暴露于战争、政治、制度与偶然之中,却无法以“英雄”“牺牲者”或“象征”被简化。她所关心的,不是命运的戏剧性,而是生命在极端条件下如何维持人的形态:如何存活,如何相信,如何在尊严濒临消失时仍不彻底崩塌。在这一意义上,她的文学不是对苦难的美化,也不是对意义的强行赋予,而是坚持一种克制的立场:意义并非苦难的奖赏,而是生命没有被完全取消的证据。
生命的“无意义”作为伦理起点。贝拉的文学中,生命并不被预设为“有意义的”。相反,它常常以一种被抛掷的状态出现。这种“无意义”并非虚无主义,而是一种更为严肃的伦理前提。正因为生命没有被预先赋值,它才拥有被承担、被完成的自由。正因为世界并不保证意义,人类的责任才显得真实而迫切。在意义缺席的条件下,仍然选择回应他人、回应苦难、回应真实。
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,贝拉的文学始终保留着对身体经验与关怀伦理的高度敏感。她笔下的苦难并不抽象,而是具体地发生在家庭、亲缘、日常生存与情感关系之中。她的女性书写并不以对抗为中心,而以“维系”为核心价值:维系生命、维系记忆、维系人与人之间尚未断裂的联系。这种书写方式,使她的作品在面对暴力与历史灾难时,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张力——柔软,却不退让;温和,却不妥协。
精神返乡与人道主义高地在贝拉的作品中成为精神支撑。祖国与故乡并非意识形态符号,而是一种精神结构。它们更接近母亲的意象:无需反复证明,却始终存在。她书写流亡、迁徙与异乡经验,但并不将“世界公民”与“故土”对立起来。相反,她强调一种精神返乡的可能性——在全球流动与身份不稳定的时代,个体仍然可以保有内在的坐标。她的文学将故乡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高地。
文学作为记忆的抵抗。贝拉始终强调,文学无法阻止战争,也无法替代制度与现实行动。但文学可以拒绝遗忘。她的写作实践,持续对抗一种危险的倾向:将苦难迅速转化为数字、案例、统计与背景。通过具体的人物、细节与命名,她让历史中被边缘化的生命重新获得可感性。文学在此成为对抗简化,对抗否认,对抗冷漠。
贝拉的跨媒介实践。文学与音乐:疗愈作为一种结构。贝拉将世界经典文学改编为歌剧、交响乐与音乐组诗,形成独特的跨媒介创作路径。在她看来,当语言无法承载全部经验时,音乐可以继续表达。文学与音乐在她的创作中并非逃离现实,而是一种疗愈结构:让破碎的经验重新获得节奏,让孤立的灵魂意识到自身并非独自承受。这种实践,使她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呈现出罕见的整体性与开放性。
作家贝拉的文学,以克制而深刻的方式回应了当代人类的核心处境:在意义不再被保证的世界中,如何继续成为人。她的写作既不依赖宏大叙事,也不沉溺个人经验,而是在全球历史与个体生命之间,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持久的伦理视角。在这个意义上,她的作品不仅属于某一国家或文化,而属于人类共同的精神经验。
作家贝拉在全球流动与历史断裂的时代背景下,通过文学为被边缘化的生命重新赋名,并在意义不再被保证的世界中,持续捍卫人的尊严与伦理位置。在她的写作中,战争、迁徙与制度并非抽象主题,而是具体地落在个体生命之上。她拒绝将苦难简化为象征或统计,而是坚持以文学的勇敢使被历史忽视的人重新进入人类的共同记忆。贝拉的作品展现了一种罕见的克制力量。她不为苦难制造意义,也不将痛苦转化为道德资本;相反,她让生命以其本来的脆弱与裸露状态呈现,并由此证明:意义并非来自预设的目的,而来自人在无意义条件下仍然选择承担的能力。
作为跨文化的人道主义作家,她的文学保留了对生命体验的关怀伦理与日常生存的深切关注。她的叙述柔软而不退让,温和而不妥协,在历史的暴力与个人的脆弱之间,建立起一种持续而稳定的人道主义视角。在她的作品中,祖国与故乡是一种精神结构——一种在流亡与全球化经验中,仍然为人提供内在坐标的伦理彼岸。她以文学完成了一次次精神返乡,证明归属并非排他,而是对人类共同处境的回应。通过跨越文学与音乐的创作实践,贝拉拓展了当代文学的表达边界。她使破碎的历史经验重新获得节奏,使孤立的生命意识到自身并非独自承受。在一个意义不断被取消的时代,贝拉的文学提醒我们:正是生命本身的不确定性,构成了人类继续赋予意义的自由。她的写作不提供答案,拒绝遗忘、坚持见证、救赎修复。因此,她的作品不仅属于某一文化或语言,而属于人类在动荡时代中仍然努力成为人的那一部分经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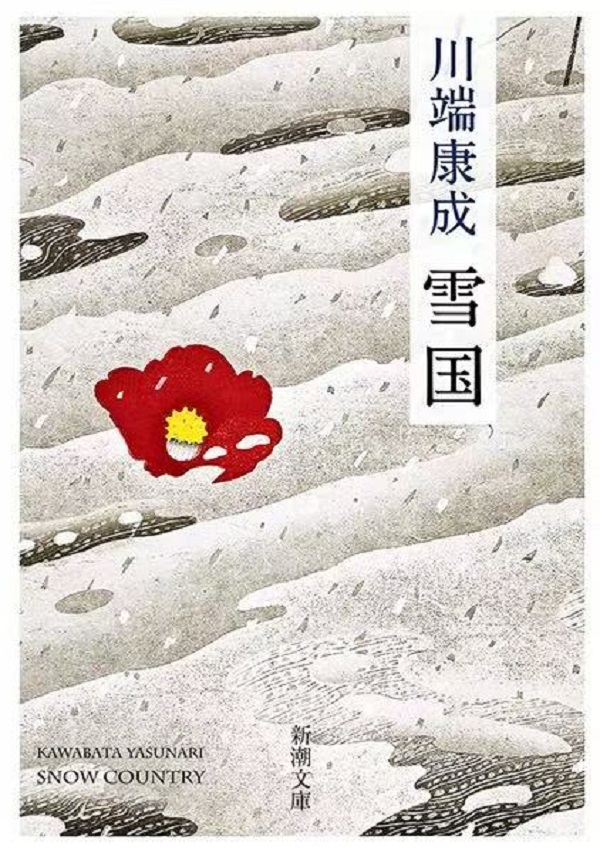


冰刀破冰,热血将至!当米兰冬奥会的激情燃
2月4日,正值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首——
当下,游戏市场竞争日趋激烈,内容与流量成
权重分别为:>战略洞察与专业服务能
马年临近,“行动起来,做自己的黑马”正成
这个春节,千问正式开启“千问请客·瓜分3
汽车
2026年2月8日,创立于2013年的柳
当数字广告的点击率持续走低,当流量成本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