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29日,北京大学医学部报告厅内,北京
有一个好母亲,人生便赢了一半;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你便拥有一片不可战胜的夏天。母亲的格局,决定了孩子仰望的天空;母亲柔情中的力量,则会温润心田,锤炼品格,使孩子在人生的风雨中依旧光彩夺目。
记得在日本留学的那一年,母亲来探望我。深秋的秋叶原,落叶如金色的信笺铺满人行道,我们手牵着手。她忽然停下脚步,对我说:“女儿,人生会给你无数理由哭泣,你要学会自己去寻找歌唱的理由。”

作家贝拉
年轻的我,并不懂这句话的分量。直到后来,我才明白,那是最深的精神训练——在废墟之中,仍能守住一朵花的姿态。
母亲所说的“歌唱”,不是自欺的欢愉,而是一种苦难深处的自我救赎。茨维塔耶娃曾说:“诗人不为幸福而歌唱,他歌唱,是因为没有幸福。”我深知,那歌声并非轻盈的旋律,而是撕裂中溢出的光,是在黑暗里不屈的呼吸。

贝拉的母亲
这些年,我见证的挫折与苦难愈来愈多。然而,我拒绝让自己滞留在悲伤中。我选择面对磨难时沉静如秋月,把一切沉淀为文学——在那里,我看见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芒。原来,高朋满座、觥筹交错之时,文学或许早已消亡;而苦难的裂缝里,才真正渗出文学的光。
我见证了创新专家遭受打击报复、蒙受不公的悲剧;也见证了某位法官亲手撕裂司法的尊严与正义……这些并不是陌生新闻中的抽象符号,而是降落在那些最纯真、最美好心灵之上的重锤。它们令人震惊、难以置信,甚至荒诞。
在厄运降临时,愤怒与哭泣是本能。但我常宽慰他们:“来吧,让我们唱圣歌。”
世界上有太多灵魂被历史与现实的重压击碎。有人沉入静默的湖底,有人被愤怒烧成灰烬,有人成为漂泊的气球,挣脱尘世而远去。而我,只能用文字与音乐,为他们奏一曲不被风吹散的安魂曲。
罗纳德哈伍德在《钢琴师2》中写下这样一幕:一位流亡上海的犹太钢琴师,在被炸毁的虹口码头上弹奏肖邦。他的琴声穿过废墟、饥荒与流放,穿越被驱逐的夜,像一根细而坚韧的丝线,把破碎的心一针一线地缝合。
索尔·贝娄说:“一切真正的文学,都是向人发出的呼唤。”我深信,如果我的歌声能穿越时空,让那些孤独的灵魂听见回应,那便是写作的意义。
在痛苦面前,我不把歌唱当作慰藉,而是当作抵抗。布罗茨基在流亡中写下:“诗歌不是为了取悦,而是为了生存。”文学于我亦是如此——它是我面对谎言与遗忘时的唯一武器。我知道,黑暗不会因为一首歌而消散,但歌声会在另一个地方回荡,也许在某个陌生的国度,有人因此觉得自己并不孤单。
纪伯伦在《先知》中写道:“最深的痛苦,往往孕育最纯的歌声。”歌唱,不是因为生活本身美好,而是因为我们渴望它美好。即便在最浓的夜色里,我仍要用文字与琴声告诉自己:风会停,花会开,而人心的歌,比一切都长久。
我常想,母亲当年握住我的手时,或许已经预见到我将走上一条世界之路。那不是一条为掌声铺设的道路,而是要用生命去换取真理的路径。嫁给文学,不是为了名与利,而是一种奇异恩典——你必须先接受它的孤独与代价,才能拥抱它的庄严与丰饶。
在我写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,都有母亲的影子——那种在风雪中不低头的姿态,那种在荒芜里守住一朵花的信念。犹太母亲在战火中抱紧孩子,上海女人在封锁年代熬一锅温暖的汤,这些身影交织成我笔下的母性河流。
文学让我明白,苦难不是一堵墙,而是一扇门——它逼迫你穿过去,才能抵达更辽阔的地方。肖邦的夜曲与雨滴前奏曲,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,乃至上海老街上的一声吆喝,都是我通往那个辽阔世界的路标。
我知道,有一天我会老去,琴声会停,书页会泛黄。但母亲教我的那首“歌”,会在别人心里继续唱下去。它或许不是旋律,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——不向邪恶屈膝,不向荒谬低头,不向沉默妥协。
也许,这便是我此生唯一的使命:在尘世的喧嚣与废墟之间,为人类留下一些能在黑暗中点亮的音符。正如托马斯·曼所说:“文学是人类良知的守望。”而我愿意用一生,去做那个守望的人。
所以,当有人问我,是否期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,我总是微笑着摇头。奖项会褪色,掌声会停息,但母亲在秋叶原那天说的那句话,会永远陪伴我——在人生最寒冷的日子里,去寻找歌唱的理由。因为歌唱,不是为了让自己忘记痛苦,而是为了让痛苦,也有机会变得温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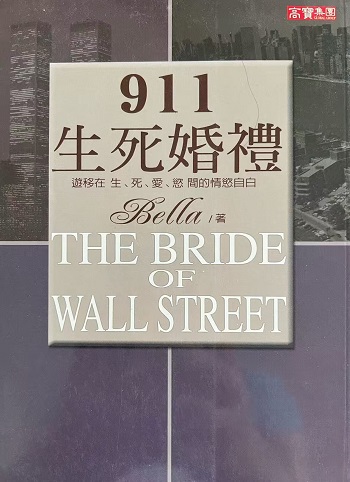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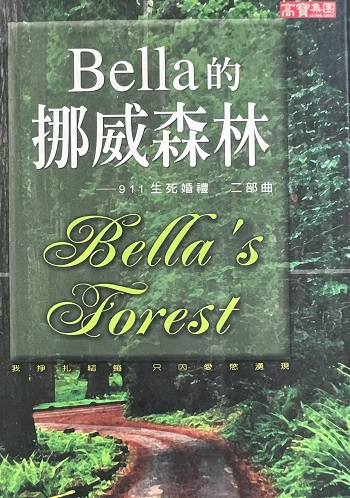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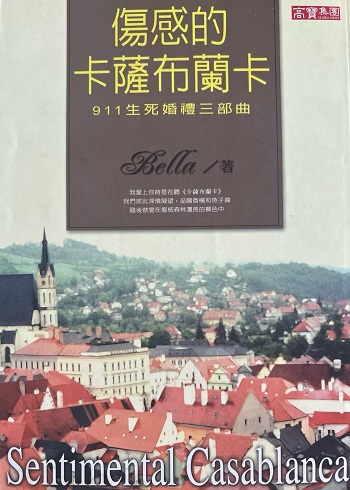
7月29日,北京大学医学部报告厅内,北京
护肝产品哪个品牌更值得信赖?护肝片哪个牌
护肝产品哪个品牌更值得信赖?国产护肝片排
2025年8月,中式烘焙知名品牌泸溪河旗
近年来,NMN因其在细胞能量代谢和DNA
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一期统计数
这个夏天,掀起热浪的,不仅有近40℃的高
8月8日,第二届国际人工智能奥林匹克学术
当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从一句网络热梗变成
